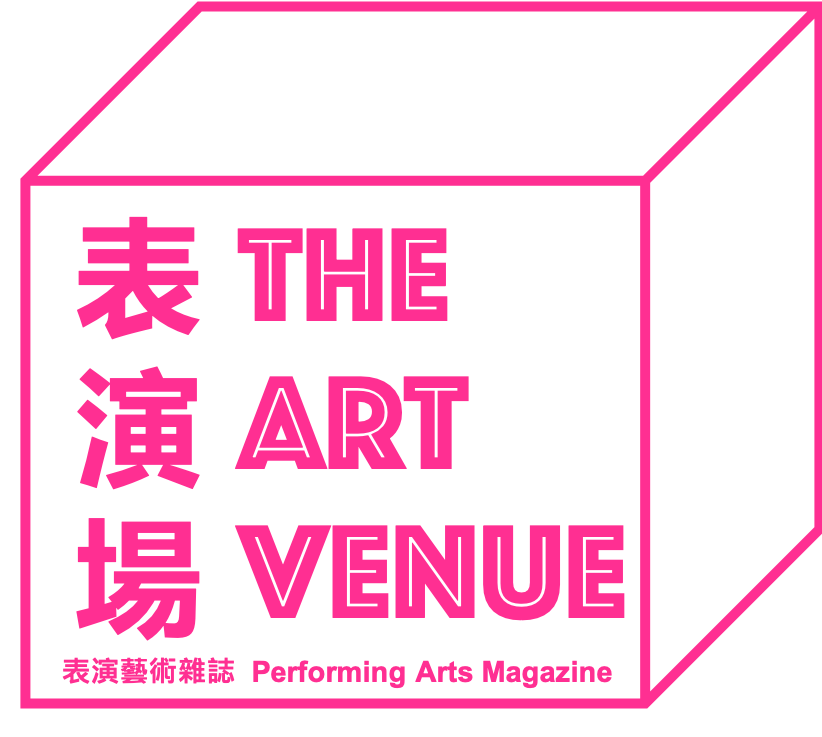專訪無言劇《李爾王》導演鄧樹榮及主角葉童 |文:何兆彬
「每天世界各地都有《李爾王》在上演,如果要演,那我要表達甚麼?而不只是多了另一齣《李爾王》?」鄧樹榮說。從2006年開始演莎劇,至今15年,每次都不一樣。他演過廣東話版《泰特斯》,更把它帶到世界各地。《李爾王》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,最新演出的改編版由全女班主演,而且是無言劇,主角李爾王一角由葉童主演。莎劇的劇力從來依靠大量語言建立,而電影/電視演員(葉童)的演出訓練也依賴對白,這麼大膽的演出,為的是甚麼?
撰文及攝影:何兆彬
全女班莎劇
「十七世紀莎士比亞的年代,沒有女性演員,戲中女性都是由年輕男性扮演的。」鄧樹榮說自己找來全女班演出,原因很多,以上歷史是其中一個原因,「最重要的原因是李爾王的長女做了一些很差的事,所以李爾王不特詛咒了他的兩個女兒,還詛咒女性!不只是他,還有幾個角色都詛咒了女性。」
因為上述這些原因,創作《李爾王》時,他也有性別上的思考,「現在已過了幾百年,世界已不同了,我忽發奇想,如果你用單一性別去做,單一男性或單一女性的去做這些角色那會怎樣?」他也曾試過以全女班演出,「其實大家都是演員,都是人,我想打破這概念,其實大家都不過是人。」
葉童說,自己對莎劇的認識很皮毛,她做了很多準備,但笑說自己並不會捧着莎士比亞來讀,「但透過老師,也會有所接觸,這個戲每次都有不同感覺,也因此我搞不懂它原文是在講甚麼。」她的準備功夫有很多方面,「例如角色的地位,身體狀況,家庭狀況都可以,而不只限於劇本裡面所寫的,每個人對這些方面都有不同看法,要看演員怎樣去豐富角色。」
演鄧樹榮的戲不同其他,他會先給你練習,事實上葉童參與這次演出,也是由練習開始,「開始時我們先做Workshop,當時沒有說我要演甚麼角色!哈哈哈!」透過Workshop的練習,樹榮漸漸確立了自己的想法,開始定下每個演員的角色,然後跟他們分配角色工作,「我們做好多練習,不論是內心的、肢體上的都做好多,有些練習我覺得與劇本是完全沒關的!但老師話要做,咪做囉!哈哈,也許日後會有用。但做完之後,也許這是身體的發掘,或擴大了視覺空間。」
對於以女子之身演設定上八十多歲的老男人李爾王,她說:「我覺得這角色沒分男女,只是權力遊戲。它是人對生命的看法,當你感到沒時間,沒能力,就更想抓住你想抓的東西!」她說故事給自己好多啟示,「這劇本是發掘人性弱點的。」
對鄧樹榮來說,問為何要演《李爾王》也許更重要,「《李爾王》被認為是莎士比亞 Crowning Piece,它是最厲害的!事實上,它是四大悲劇中比較深層的,《哈姆雷特》寫的是年輕人,大部份人喜歡它激情,少有人喜歡接觸《李爾王》的衰老,所以它給我的除了人性慾望,也有它的年紀!」他說,《馬克白》和《奧賽羅》寫的是中年,主角上下都有人,而《李爾王》則是眾人之上,「本來所有人都在你下面,但你做錯了一個決定,令你處於谷底。哈姆雷特雖然是王子,但沒有人聽他的,他只好發動一個革命!」
葉童:抱着學習心態
葉童其實早跟鄧樹榮合作過,那是1997年,橫跨回歸期間,當時演的是春天製作《上海之夜》。一隔二十年,二人在2019年再合作,演《死人的手機》,分別自然很大,「我一直有關注他,覺得他很特別,也喜歡他的簡約,激發你的想像空間,你的內在。在沒有包裝的演出,一切會更原始,更真實。」
她說自己我沒接觸過這戲種,是抱着學習的心態來演,「《上海之夜》是以商業考量為主,我不因為它有甚麼提昇,也許因為過了這麼多年,我對藝術也有了不同要求,《李爾王》對我來說是提昇。它也是好好的機會,讓我來感受劇情概念。我喜歡接觸舞台的感覺,它讓我認識到不同空間,但我經驗淺,沒這方面訓練。」
翻開時間囊,鄧樹榮記得《上海之夜》後,自己在藝術路上也發生了很多變化,開闢出自己的路,「自從《上海之夜》,我也進入了另一階段,我問劇場是甚麼?為何要演?在香港演有甚麼意義?本來高志森想找我演《聊齋》,但我拿了獎學金去了升學。到了99年我有一個委約節目,回來想做木偶,我想追求一種形式,而不只是做劇本。」九十年代末期香港流行多媒體劇場,他也參與過,但跟主流不同,他開始思考的是藝術上的減法,而非加法,「很多行家的前設就是多媒體,但我不這麼認為,它只是手段。98-04年我開始接觸瑜伽,一直在練習,04年去了印度學習,回來後有很大的改變,瑜伽跟我在法國Poor Theater的學習產生了共鳴,Jerzy Grotowki提出劇場是演員跟觀眾的能量交流,其餘都是次要。瑜伽是靈修,把不大重要的刪走。」
於是自從2004,他進了演藝學院教學,同時把瑜伽放進了表演,在七年之間,在表演上建立了另一種風格,越演越簡約,語言有時變得次要,「那即是前語言,離開演藝學院後我創了自己的藝團,那又是另一階段,例如做《泰特斯》或《死人的手機》,也開始做莎劇,得着好大。」
動作、速度和內在
劇中沒有對白,只靠肢體或動作來表達,「無言劇由來已久,在西方Mime(啞劇)有兩種,一種是Pantomine Mime(默劇),例如拉繩模牆這些;另一種叫Corporeal Mime(形體默劇),你會用整個身體去表達你的State of Being(生存狀態),而不只是動作,它們都跟前語言有關,來源都是舞蹈。幾十年前,學Mime一定要先學舞蹈。」
《李爾王》是無言劇,但莎劇的力量一直來自對白,把語言抽空,好處壞處是怎樣?「莎劇的基礎是語言,這沒有疑問!但它只是透過語言,去讓觀眾看到Invisible (隱藏)的事物。這次是實驗,它是一種方式,是否能呈現原本有語言的精神?這是一種實驗。」
演員演來又怎說?葉童:「有時演戲,好多對白都是交代的,我有少少不大認同,所以這一次以動作表達,會更加給予直接感受我自己或觀眾,而不用說:這是蛋炒飯。它很直接。人生出來沒有語言的,嬰。會用表情或哭聲,演員怎去表達?它令我重拾自己的生存技能,重新把它找回來。」她說這麼一來,對自己形體上很大考驗,「我不會當自己是舞蹈家,那是不可能的,我也不是體操、運動員,但它怎令你有感覺、認同,我要透過感受去呈現那動作,這是我的方向,有時我也會想,要不要設計一個動作?老師有時覺得未必對,會太做作。」
採訪前正值演出前一日。她排練了好一陣子,她的領會,是除了身體,動作及速度外,也有內在表達,觀眾還是會感受得到,「由於無言,你要用身體或內部去表達,速度快慢也是表達的一種。」首次這麼演出,會有疑惑嗎?「之前好多疑問的,是有啊!好多東西、要求都不明白,只有去試囉,現在似乎已找到方向。」作為四大悲劇,抽掉語言,其悲劇性又變得如何?「我們是有一點改動,但劇本的精神分別不大,但想呈現的是共通的。如果你想像它會呼天搶地,我們未必是這樣。」
橫跨歐洲的莎劇節
《李爾王》本來是香港莎劇節節目之一,莎劇節由鄧樹榮工作室舉辦,本來於去年年底舉行,因應疫情,延至今年,但由於還未通關,也一延再延。結果他決定先把當中的兩個莎劇,包括自己執導的《李爾王》率先演出,「搞莎劇節有段故。2012年,我把《泰特斯》帶到倫敦的環球莎劇節演出,當時他們請來37隊國際隊伍,代表中文的只有我們,跟中國國家話劇院演《李察三世》。我們能夠代表粵語,這是很大的榮幸。」
因為這次演出,他發現歐洲有好多莎劇節,「我們不斷參加,見識到他們十幾個城市組成聯網,不同城市每個月都有交流。我怱發奇想,能否在香港也搞一個莎劇節,與歐洲有聯繫?」
是因為這樣,他開始寫計劃書,拿資助,香港莎劇節一步步形成,但同時卻遇上了疫情,演出一再受阻。
為何莎劇經歷四百多年,仍然強大?「由2006年開始到現在,我們已是第四次演出,它不只是吸引我,而是吸引到對生命提問的人。莎士比亞描述生命準確,但從來不去解釋,解釋你就是單面,而人生好多悲劇就是去解釋,把自己的解釋放在別人的生命裡。它的偉大是不解釋,但描述得精準深入,深入到你驚。所以撇開它的語言、力量,是它對世界的描述之精準。」他說,無論你從事何種表演藝術,都建議你去研究一下莎劇,總有得着。
要了解莎劇,可不容易,原著用的都是幾百年前的早期現代英語,「它有很多改編,黑澤明《亂》就是《李爾王》,《夢斷城西》就是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,Orson Welles也改編過。很多藝術形式都有表達莎劇的影響。」
但他說,要了解原著,一定要排除萬難,「去讀原著,讀完就是成功,但你肯不肯花時間去讀?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