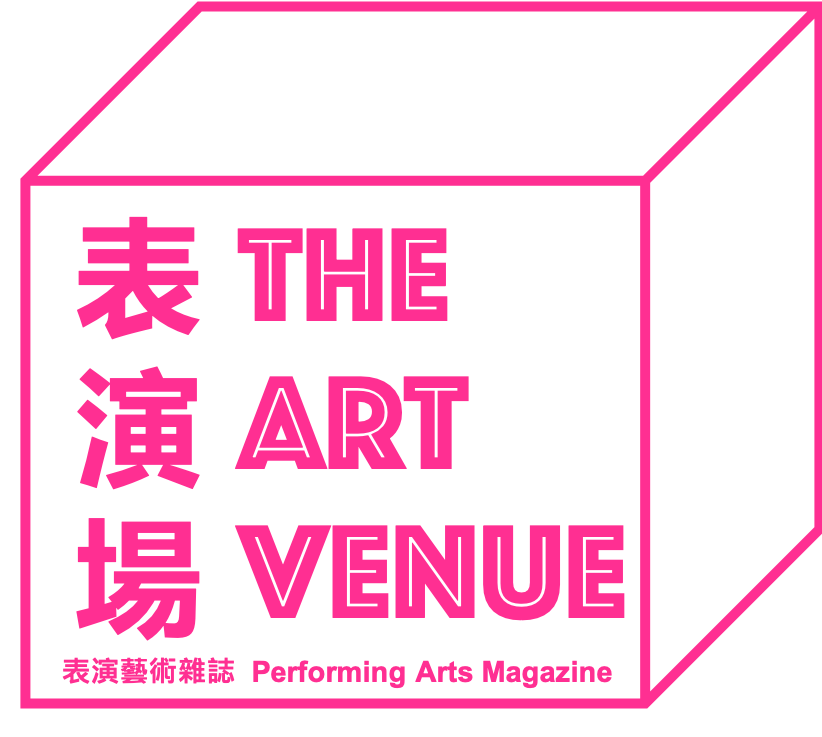年月對舞者的磨煉 專訪莫嫣 x 喬楊 | 何兆彬
(照片由城市當代舞蹈團提供)
要數香港的編舞家,梅卓燕、伍宇烈外,你還會數到誰?「上一代的他們成名已久,相比下,我們不上不下,而下面20歲左右的舞者也上來了,我們這些中生代,可以怎樣呢?」舞蹈藝術家莫嫣(Jennifer)說。她由17歲開始進演藝學院,畢業後曾在城市當代舞蹈團(CCDC)當了七年全職舞者,離開後獨自闖蕩。這次回來,參與《42‧36‧42》的編舞工作,與資深的喬楊合作,共舞十多分鐘。她要找到的,是在這個青壯年歲,自己在香港舞蹈界的定位。
TEXT & PHOTOGRAPHY: 何兆彬
舞蹈界中生代
CCDC 2021年舞季首個節目《42‧36‧42》邀請三個中生代舞蹈家,各編一個小品。當中有李思颺的〈快樂頌〉(Ode to Joy),有Jennifer的〈花從蘇菲的世界路過〉(Sophie’s Garden),也有黃振邦〈餘音裊裊〉(Listen Carefully)。節目叫《42‧36‧42》,42及36其實正是三位編舞者的年齡,Jennifer行年36,是較年輕的一位,「年齡在亞洲舞者來說是重要的事,尤其在傳統中國舞、芭蕾舞,30歲左右就要退休。」她說:「當代舞的界線沒那麼大,但對表演者來說,年紀漸長也是個挑戰。當你到了另一位置,我們應該做點甚麼?」
她說像自己一直在當代舞蹈界活躍,一直跳一直創作,做自己相信的事,「但為何有一段長時間,中生代整個階層好像消失了?是不是每個行業都這樣?」
她憶起節目的起緣,「當Yuri(伍宇烈,城市當代舞蹈團第四代藝術總監)來找我時,他提議不如找我跟喬楊合作,排一支舞給她跳,應該會有趣的。從前我還在團裡時,跟喬楊一起七年,大家演過三次母女,我們是有一種特別緣份。」最初伍宇烈提出給喬楊排一支獨舞,但當她開始獨自創作,不斷嘗試,結果二人互相碰撞,卻撞出了另一個結果,「因為我不斷問點解,她覺得很困擾,對她來說,我問的那些都不是問題,毋須糾結。但對我來說,我想找答案,後來排得越久,連她也想要答案。這支本來是獨舞,後來她就提出,不如我們共舞吧!」
喬楊的捨棄
舞蹈叫〈花從蘇菲的世界路過〉,蘇菲即Sophie,乃喬楊的洋名,花即Jennifer(莫嫣)自己。共舞時,喬楊在一個圓圈內走動,不住走動,舞到最後都不出此圈,Jennifer則在另一個小圈——內圈中舞動,二人姿態不同,但舞時各有互動。
Jennifer說她一早已創作了一個圓圈,由獨舞變共舞,維持了圓圈這概念,「她在圓圈內跳,我加入主要是回應她的動作,跟她共舞。我回來(CCDC)發現又熟悉又陌生,這個地方為何不同了?場景一樣,但人面全非,一邊想,一邊勾起了好多問題,例如跳來跳去,我都是這樣跳舞,還有甚麼可能性?如果不是,那該怎定義跳舞?」最後她決定不如以舞姿去回應喬楊的動作,「我不做平常我的動作,只是用日常的動作去回應她。」二人坦誠交流,喬楊說自己跳了幾十年舞,從來沒有跳過這樣的圓圈,也算是創舉。
photography:何兆彬
回到起點,最初創作這舞,Jennifer總想起喬楊的修養,想由此出發。喬楊本是陝西人,她由23歲開始習當代舞,1996年加入CCDC,迄今跳了二十多三十年,如今快57歲了,狀態仍然很好。Jennifer觀察喬楊為了藝術,也為了延長自己的藝術生命,平常相當著重自己的身體,每天早睡早起,生活規律,當中做了不少捨棄,「很少年輕舞者會這樣照顧自己,整個團只有她做得到。另外,她的壓台感很厲害,也是整個團只有她做得到。」
喬楊笑笑,說每個舞者都有自己特色,她謙稱:「我的特色就是沒甚麼特色,我只是喜愛舞台。」她每天六時半起床,公司每早九時半的早課,她九時就準備好了,一個半小時的早課她天天上足,這樣的生活,已過了十幾二十年,從不厭倦。
「我跟其他舞者的年齡差距很大,大得離譜!她們有的98年出生,我64年出生,相差小的十幾歲,多的三十幾歲!但我們沒有代溝。」資歷上的差別,對表演總有影響吧?「說沒差,是有啦。因為經驗,我知道怎樣處理身體,知道自己缺了甚麼。不是年輕人不好,而是外間誘惑太多了。」
沒想到一跳30年
「我根本沒有想過跳到今天。」談自己半生在舞台,喬楊坦白地說。她生於1964年,出生不久就遇上文化大革命,她從12歲開始學中國舞,身體質素好,老師從不管她,「我軟度好,沒有受過罪。」憶起童年,她總想起自己生性好動,跳舞跳得開心,很快就被保送到寶雞市歌舞團,「因為當年文革,姐姐都被送到上山下鄉,生活很苦,爸爸媽媽見狀不想我那樣,覺得我還是去學跳舞吧。而且我12歲就領18塊錢一個月,很不得了,當時我爸一個月才40塊!」
23歲那年,她得悉好些美國人正來廣東談合作,要開現代舞班,開始在各地招生。「我知道中國舞怎跳,知道芭蕾舞怎跳,但現代舞是甚麼?」她很好奇,決定辭工,甚麼都不要,就是要往廣東一行。
結果此行一去就考上了,從此打開了天地,「一學現代舞就覺得很自由,原本我學的是傳統舞,只能在地上一下下,但現在我很能抒發自己。中國舞會框住你自己,失去很多個性,而且現代舞不用笑!很Cool,很舒服,我在台上不喜歡笑。」在現代舞裡,她找到了自己。
因為曹誠淵也是廣東現代舞團的藝術顧問,常去看他們演出,喬楊因此認識了她的丈夫——他當時正在CCDC當行政總監。二人1994年結婚,她30歲來港,1996年加入CCDC,「當年女孩很多,後來有人結婚生子,我沒想到自己一跳就20多年了。」
舞蹈界畢竟需要大量體力,一般舞者到了一定年紀,就開始編舞,漸漸淡出幕前,喬楊選擇了更難走的路,一直跳下去,但對她來說,這個選擇反而輕鬆自然,「編舞對我來說壓力太大,她(Jennifer)一邊編一邊會哭。我去做瑜伽,做很多自我建設,把自己變得多元化一點。否則看CCDC的人來看了二十幾年,如果你老是沒變化,都不來看你了。所以一定要學,學無止境。」她客串過教班,但自己更喜歡的是私下教授年輕人怎樣照顧身體。
編舞狂哭
Jennifer也坦言自己從小想的是跳舞,當初也沒想過要編舞,「我一開始就知道自己要做Dancer,後來有修教學,也是因為知道老了要教學。後來我入了團,有很多問題,到我離開後做創作,也不是有很強烈的創作動機,而是恰好有一次東邊舞蹈團的余仁華先生問我,你已離開了CCDC,想要幹甚麼?我隨口就答:我要編舞!沒想到他就給了我編舞機會。」
這樣子她開始了創作,轉換身份看同一事件,也喜歡了這個轉變,這次回歸CCDC,身份不同,又因為編舞期間,將獨舞變成了共舞,壓力爆標,採訪前一周情緒低落,「上星期喬媽一來我就哭了,我說(舞蹈)又要改了。我不是每次都會這樣,而是因為這次我自己要跳,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表演者,可以一邊跳一邊看到整個Picture,我做不到。因為我要即時回應喬媽的動作,當中有一半以上的舞姿是即興的,已超出了我的負荷,另外還要計算雙方距離,看當日的Energy,才決定怎樣Feedback。」對自己的要求,變成千斤重擔,壓在自己身上。
對藝術工作者而言,36歲是一個怎樣的年齡狀態?Jennifer坦言從前一直沒有很有野心的經營,因為一直有不同工作,有舞就編,有舞就跳——總是想「遲些再算吧。」但經歷這一次她影響很大,「可能真的要找一個題目去做研究。年齡也有關係吧,有天起床,你會突然覺得自己沒有時間了,但是怎樣的沒有時間?我也說不上來。」
訪問中,她最初問到自己,像她們這個中生代到了另一位置,總在思考應該做點甚麼?有了這次體驗,她應該很快就會找到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