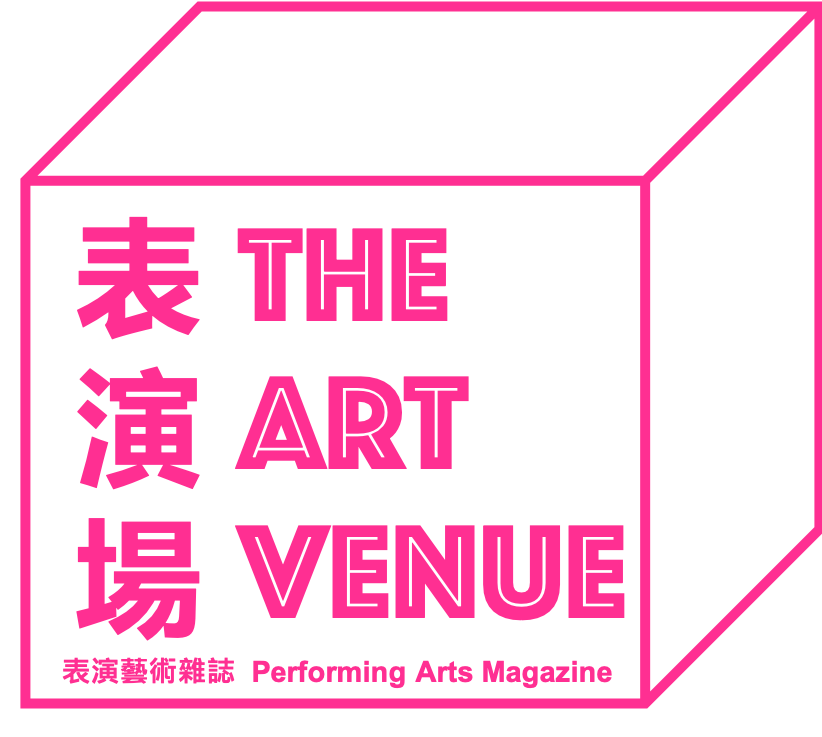從過渡的剎那、 到精神之永恆 前北藝大校長邱坤良教授 《風華不盡關渡元年1991藝術大移動》
從過渡的剎那、到精神之永恆1
1 本文參考邱坤良教授《風華不盡關渡元年1991 藝術大移動》寫成,在此特別感謝邱教授在書籍未出版前慷慨提供書稿。然文章若有描寫不周之處,作者當自負全責。
文/張敦智
1982年,國立藝術學院(今臺北藝術大學)成立。由於位在關渡的預定校地仍處整地、招標工程階段,師生們於是長期在大台北地區四處借空間上課,與土地、自然、民間為伍。經過長達九年的非常時期,收到校園可正式啟用的消息後,院長、戲劇系主任等人決定交由邱坤良老師策劃一齣「戲」,讓全校告別暫居的故土,前往等待已久的關渡校地。當時,在蘆洲已「借住」五、六年的空間雖然有限,但三、五百位學生窩在一起,還頗有家的感覺。面對這項全校性大事,邱坤良開始思索:如何做一齣「搬家」的戲?
「搬家」意味著:告別、遷徙、流亡、與離散。是人生中的不得不,也是整理、肩負起深沈過去,朝未知境地披荊斬棘的過程。這也是為什麼民間習俗往往對搬家慎重其事,要探勘風水、擇定良辰吉日,入住後也要安神、安床,透過不同方法驅凶祈福。荷蘭社會學家 Van Gennep 以「通過儀式」(Rites of Passage)理論指出:人生需要渡過的關口(C r i s e s)包括出生、成年、結婚、死亡等,各都隱含分離、過渡、與重新聚合的多重意義;而儀式往往幫助人們從心靈上通過這些轉折與危機。再者,「關渡」本身是關口、隘口之義,在此情境下,它變得不僅只是名詞,更是動詞。統整以上思考,這齣儀式劇場正式命名為《關渡元年1991》,邱坤良決定讓學生們實際「出走」,脫離原先熟悉的環境,向土地、以及土地之上的人們學習,整合所見所聞,最後完成「出蘆入關」。
為落實構想,他聯絡大甲鎮瀾宮,爭取讓同學們演出平時由民間劇團負責的「隨駕戲」,對方同意之餘,不禁直呼「學生會很累!」。就這樣,所有人緊鑼密鼓地開始練習「扮仙」儀式劇與相關知識、技能。在八天七夜隨駕出巡的過程,除了起程「起駕」與回鑾「落轎」需在大甲鎮瀾宮前演出,途經彰化天后宮、北斗奠安宮、西螺福興宮等地,也要演戲請神祗落轎。此外,沿途民眾亦可登記請劇團扮「私」仙給予家族祝福。這樣充滿機動性、卻也無比神聖的責任,全落在當時這批莘莘學子身上,無論對技術、體力、以及儀式領悟度都是極大考驗。搬演野台戲的過程,觀眾上至神祇,下及熙來攘往的信徒。同學設法在許可範圍內揮灑創意,來去目光間,有民眾直接對台上演員大吼「無聊!」,首當其衝的同學多年後回想,覺得這比「黑特劇場」還狠、還直接。
上述隨駕遶境屬於《關渡元年1991》中「朝香獻供」的部分。事實上,整齣儀式劇場橫跨半年,足跡遍及臺北、新北、宜蘭、臺中、雲林、嘉義。在開場於蘆洲校區「大張旗鼓」祈福後,經「朝香獻供」,臨別前兩天再向蘆洲當地宮廟與鄉親父老致謝、告別,是為「謝境呈戲」;而5月11、12日兩天的「出蘆入關」遊行表演,除了全校動員,更有許多校外團體共襄盛舉。值得一提的是,遊行當天,來自美國的服裝設計老師龐珊(Alexandra B. Bonds)亮出籌備已久的「秘密武器」:以校內不同師長為原型製作的「八仙」大型魁儡,每「仙」需動用五至六名學生才能舉起,揉和傳統陣頭文化與現代元素,令校內師生與沿街民眾大開眼界。最後,進到關渡校園內「安土淨壇」,音樂、舞蹈、美術各系紛紛舉辦自己的慶祝活動,接著「闔堂圓滿」,告一段落。
一轉眼,關渡元年已經過了三十年。當初平整、綿延的天際線,如今穿插著高樓林立。這些年來,面對大學暴增、政策轉彎、籌措經費、及增設系所等挑戰,學校需仰賴世世代代的有心人們才能掌握方向。藝術教育本來就是門「虧本」生意,它很可能無法換得萬貫財富,卻無形傳承著勇於提供不同視野看待社會的精神。正是這種精神,隱隱推動著歷
來各種轉捩,讓藝術在時間的長河裡如蔓生雜草,無所不在,柔軟、且強悍。北藝大應該一直是這些藝術家們的搖籃,無論關渡元年,或關渡萬年。
嗚謝:本文照片由邱坤良教授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