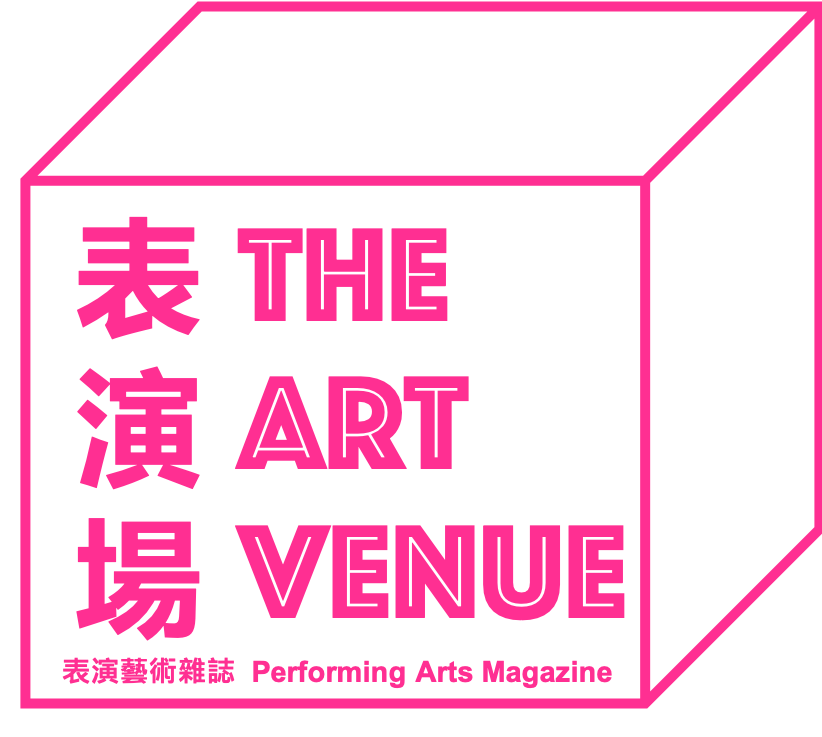表演場第十六期 -蔡明亮專訪:觀眾開始不害怕我的電影
良夜:蔡明亮的電影、音樂交流與即興創作
蔡明亮專訪:觀眾開始不害怕我的電影
1957年出生於馬來西亞,為台灣新電影運動以來最具代表性的電影導演之一。
1994年以《愛情萬歲》奪下威尼斯金獅獎,奠定世界影壇地位,之後亦獲藝術界青睞,於台北、威尼斯、上海、名古屋等地推出展演及跨界創作。2009年作品《臉》成為羅浮宮首度典藏電影,創下藝術電影的標竿與典範。2012年展開「慢走長征」影像創作計劃,至今已完成七部短片作品。2013年憑《郊遊》再獲威尼斯評審團大獎。2014年受布魯塞爾、維也納、台北與光州等藝術節邀請,推出舞台劇《玄奘》;同年於臺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展出《來美術館郊遊》,寫下電影走進美術館的歷史創舉。
去年首次參與「台灣月」的蔡導,為香港觀眾帶來了「《我行且歌》蔡明亮的影像與說唱」,受到熱烈迴響。今年他再度於「台灣月」登場,將會帶來《良夜:蔡明亮的電影、音樂交流與即興創作》。場主非常榮幸能訪問蔡導,談談他的創作想法及今次的節目。
圖片提供:汯呄霖電影 攝影:張鍾元
表:為什麼會有即興創作這個構思?
蔡:創作就是不停在發生和發展的事情,作品對我不是一個製造的概念,也不是為了製造一個作品。創作是源於生活經驗、體驗和感受,它自己會長出來。這不是一個針對市場的概念。其實我的作品也面對很多考驗,比如說在開始這個行業時,一定會面對生存的問題。可是當你發現你的作品不是大眾化時,或者性質不是大眾化的東西時,但你仍然還是在這個行業裏面時,後來會發現其實還蠻開心的,因為自己還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,不要附和別人的規定。但不附和別人的同時,要去創造新的契機或者新的一種生存方式。所以,後來慢慢我的電影好像是比較是有生命的東西。經過幾年後,一個電影會發展出另一種面貌,它的受眾也不太一樣。你會發現你寫的東西可以給每個時代的人。比如說我去威尼斯,他們邀請我們重映舊作時,不只是一個修復的概念,和16年前的版本來一個競賽。他們認為這個作品有它重新被認定的一個可能。因為修復的概念,又重新被看一次,被新時代的人看一次。到我自己處理的時候,我一定會想,我要怎麼被看到,這個作品怎麼被使用,和16年前不一樣。因為我一直在發展我的創作概念和使用方式也不一樣。所以,這次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找我的時候,我是延續去年的東西,我去年使用一個唱歌的方式當成節目來做,因為在台灣做展覽或者在做演講的時候,特別在做展覽的時候,我常常會用我的一些觀影經驗、或者聽音樂的經驗、或者生活的經驗分享給觀眾。
分享的概念其實也是一種展示,為什麼這個作者會做成這個作品,他一定是從某個地方走過來的,這不是冒出來,也不是想出來的。所以唱歌這個事情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表達的其中一個方式,它是一個元素來的,但是,是什麼歌呢?一定是我自己的經驗,我覺得有感情的。從我會聽音樂開始,我就聽國語老歌,那時我才是小孩子,後來發現那個歌跟時間有微妙關係,但不是說那個歌老了和懷舊,而是它有一些能力釋放出來,是響應現在的社會。現在的社會結構是不太一樣,所以可能老歌,也有一個新的發展。
我把做電影發展成一個展演的概念。不是放映而已,還有一個表演在裡面,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包裝。人們不只是進戲院而已,而是覺得買票進戲院好像去了美術館一樣。像光華邀請我去唱歌,他們知道我會分享一些老歌,我把老歌變成一塊東西,有很多記憶在裡面。所以電影裡面的歌就變成我創作的元素,我必須要告訴觀眾為什麼這個會用老歌,對於年輕人來說這些老歌都是新歌,其實這些老歌很久以前就已經被創作出來了,也很可能這些歌被封箱了,不太可能被使用、被遺忘了。所以我用它時候,它會發生一個新的作用。
我去年的作法是我還是用一個記憶的概念,我把我對老歌的記憶,對老明星的記憶,或者老電影的記憶變成一套作品。但是使用一種表演的方式來發表的,它演過就沒有了。所以那一次就蠻開心,因為有些東西被喚醒。
今年光華又找我,我就跟光華講說要給我時間做一個作品,因為這些歌藏在我的細胞裡面,血液裡面,可是我要變成作品就要一個過程轉換,這次創作的狀態裡面,不是先有作品,而是先有一個過程的呈現。我會針對這次做一點影像的東西,通過這些老歌做一個暖身。其實這個分享很好玩,告訴觀眾我要把這些記憶慢慢找回來,把一些感覺找回來。同時,我也在透過一個創作找自己的感覺,這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發表。
表:香港觀眾都較被動,你會怎麼與他們互動呢?
蔡:我覺得我們不能想觀眾是誰,現在的年輕人也有自己的經驗。所以我覺得這東西,我只是提供了我自己的一些經驗。讓他們理解這個導演經歷過怎樣的一個社會,變成現在的狀態。也許還有經過一些磨難。我覺得現在觀眾越來越厲害了,越來越聰明。他們也是受過訓練,如果他知道蔡明亮今天有一個活動,他已經有事先了解,所以好像不用擔心他們的理解和他們來不來的問題。過去幾年大家很認真做這些事情,已經累積了一定聲譽了,大家知道台灣月也就是在代表台灣人的創作。所以就不想太多。
台灣滿有趣是它當代美術館很多,我們的時代是沒有美術館的,沒有美術活動,那個時候比較貧瘠。這幾年我為什麼會轉到美術館?因為電影在電影院是沒有宣傳空間的,這樣的話,觀眾也沒有機會被培養到甚麼東西。美術館是一個新的空間,那他養成一批比較開放、比較柔軟、比較包容的觀眾。
我們的觀眾就知道娛樂,好像聽到藝術就很害怕。那美術館是一個培育的場地。你做什麼都好,只要你的層次被他們接收了,對觀眾來說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教育、美術教育。我用的東西就是很普通的,像老歌,是被千錘百鍊,都是經典的歌;老歌其實是把我們整個時代包括起來,時代的氛圍、時代的狀態,跟現在不一樣。那我在想,希望把老歌變成一個新的可能性,也是可以進到藝術殿堂的。很多經典,其實你回頭看,你就覺得你不用他太可惜了,它可以放到藝術殿堂,重新讓你感受它的力量,那我就深深受到它的影響,所以我就掏出來包裝,讓新一輩的人理解到它的精髓了,就給他們嘗試和多了解一下,不要當成消費,用互動的方式啟發觀眾。把舊的東西重新包裝,啟發觀眾去看以前的事。
像我在威尼斯的展演,除了它的電影之外,那些參與者來聽我講60到80年代,我童年的時候,整個電影或音樂過程。所以對他們來說,他們也要知道為什麼那些電影會發展到現在這個狀態和這個樣子。
所以整個來說,到了香港以後我也會繼續發展各種可能性,其實就跟觀眾互動。以前的發展就像一個畫展,你畫完畫,別人就走了,我的發展就比較不一樣,我永遠讓作者跟作品綁在一起,它有一個更大的能量掏出來,你就沒有什麼藉口說你看不懂了。那個作者就坐在這邊,你問他呀。他可以展現給你看這個作品為什麼是這樣的樣子的。
這個關係很好,我覺得很多台灣觀眾開始不害怕我的電影,我的創作。很多人開始靠近過來,因為我做了這些事情,起碼看到我的熱誠。
對我來說,我就是喝港台電影的奶水長大的一個電影人,或者一個創作人,就是我看到那一個年代沒有網路,我那個年代我家沒有電視的,我到後來才有電視的。所以我完全是在電影院或者在聽電台的概念。但它的確是豐富了我,提供我一個快樂的童年、少年、也提供我一個創作的概念。但是呢,它也同時讓我發現我那個時代有很多侷限,那時商業片很重要,他是樹林。也有好的,沒有太多不好。我們那個時代就是要消費。所以我就要把那些好的再提出來。你認真去找的時候,會發現老歌有很多寶藏。電影有很多好的老電影。如果有機會一直被使用,你就會覺得能發揮它的那些功能了。
圖片提供:汯呄霖電影 攝影:張鍾元
良夜:蔡明亮的電影、 音樂交流與即興創作
日期時間:19.11.2019 (星期二) 19:00
活動地點: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力寶展藝場
公眾報名免費入場:網上報名
*本活動將以影像放映、時代曲分享以及藝 術家現場即興創作方式進行。開演前15分鐘開放入座,歡迎現場候位。